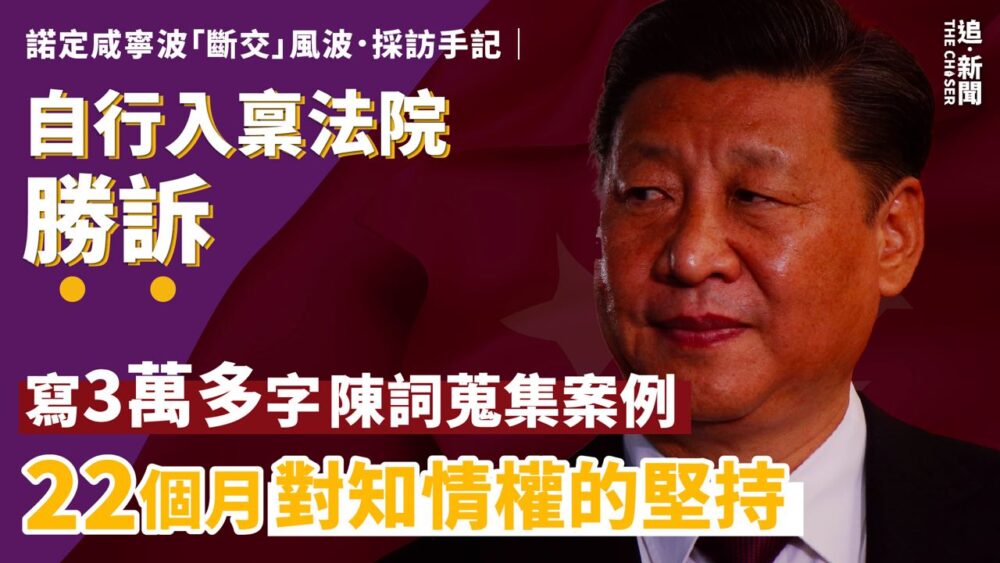
「頂!咪搞啦,聖誕正日就出嚟食飯,死仔包!」中學朋友們遠道而來,他們歡聲笑語間,室友聲線隨羊腩煲的香味,從客廳飄進房間。
檯燈淡黃光暈撥開房間一隅昏喑,桌面歪歪斜斜立着10個以上被壓扁的能量飲料空罐,滿地紙張承載紅筆和螢光筆的符咒。我每日空餘花上近8小時,雙眼頂着黑眼圈,在短短4星期上訴時限裏,殫精竭慮埋首電腦,焦慮地研究過往案例、資訊專員公署指引、市府憲章和規程等文件,鑽研可提出的上訴理據,最後提煉潤飾成1萬多字入稟狀,備妥我方150頁證據(exhibit)在個案文件冊(case bundle)一併供初級裁判法院(First-tier Tribunal)考慮。
「哎呀,你哋食啦,唔洗等我。」上訴死線很不幸地落在2023年聖誕節後天,時間正在倒數,我瘋狂敲打鍵盤,頭也不回倉卒地説。夢回那年5月立夏,我還是名英國新聞系三年級生,從展開調查到三度被市府和公署拒絕披露資料,走到半年後只餘入稟法院一途,再到上訴得直並於上月刊出報道,期間我多次向法庭提交書面陳詞,回應當局的質疑和反對,歷時共22個月。這是趟艱難疲憊的修行:時間不充裕也倒算有,但我不僅初出茅廬沒有資源,亦不諳法律,而公署更有律師坐鎮——最後與我對戰的律師職銜是「公署法律部主管(《資訊自由法》)」。
報道無罪 知情有價 請即訂閱《追新聞》:
https://www.patreon.com/thechasernews
一路走來提交法庭的陳詞累計寫下3萬多字,個案文件冊最後達600多頁,固然在爭奪機密文件本身,但更重要是圍繞知情權的激烈攻防,以及推而廣之其背後公眾利益。如果英媒為英國公眾服務,而港人是當中少數族裔,難受主流關注(英國地區傳媒資源也捉襟見肘),那麼我作為香港記者,便尤其肩負對在英港人社羣的責任——至少很理想地説:監察當局行使公權力時如何切身影響或忽略港人,並透過新聞賦權(empower)他們了解地區政治以至參與公民社會。市府「斷交」決定正確與否自有公論,這亦不是作為記者關心的重點。但公眾能夠在知情前提下,討論和決定公共議題,選擇投票將權力交予誰,卻是民主的基石。
我不敢自詡更不是大衞,公署和市府亦不是甚麼敵人,但它們肯定似歌利亞裝備精良。累,真的很累。深深慶幸的是,我的書面陳詞最後獲法官形容為「雄辯(eloquent)」和「連貫(coherent)」,至少打了一場漂亮的仗。
甫開始時,我更像初生之犢,跌跌碰碰從零開始,實務和抽象並行瘋狂自學,惟恐有所遺漏:用甚麼網站找過往案例?《2009年地區民主、經濟發展和建設法》和其他法例怎樣應用於本案?上級法院哪個裁決約束或有利於我上訴?怎樣應用公法中的「相稱性(proportionality)」?法院過去如何詮釋《資訊自由法》下「持有(hold)」和「代為持有(held on behalf)」的法例要求?如何衡量公眾利益的平衡性測試(balancing test)?為甚麼諾定咸大學指稱商業損害時,未能證「因果關係(causative links)」,反而是滑坡謬誤?為甚麼所謂工黨市議員們內部會議的形式和目的,實際上反映他們在履行市府公共職能?甚至連怎樣用牛津大學法律權威引用標準(OSCOLA)標註案例,我也要從頭學習,林林總總恕難盡數臚列。
提交的各項論據中,我曾質疑市府陳詞似是而非,在和其他城市「斷交」作正式行政決定時,未有遵守其具法律效力憲章的既定程序;但今次卻反而稱,只有遵守程序的才是正式決定,才受《資訊自由法》規限。此外,我提出一系列論據,強調披露資料的公眾利益凌駕於保密,如校方其時被英媒指控自我審查寧波校舍的教材和教職員言論等等,更印證資訊公開的重要。
美國《華盛頓郵報》前發行人、已故著名報人凱瑟琳.葛蘭姆(Katharine Graham):
「新聞是有人不想公之於世的事,其餘的皆是宣傳
(News is what someone wants suppressed. Everything else is advertising.)」。
「一些人對此不依不饒,要求市議會披露決定參考的相關文件並就此訴至法院。」官媒《環球時報》如此形容我的調查報道。如果「不依不饒」意指為求真糾纏不休,那我或許是吧。但記者天職從來都是提出問題,哪怕它們可能會煩擾惹惱當權者。猶記得入學初,耄耋之年的教授向我們提起一句名言,出自美國《華盛頓郵報》前發行人、已故著名報人凱瑟琳.葛蘭姆(Katharine Graham):「新聞是有人不想公之於世的事,其餘的皆是宣傳(News is what someone wants suppressed. Everything else is advertising.)」。
由始至終,我初心非常純粹。決策過程從沒有任何公開資料,即便市府曾多番公開指歡迎與發起聯署的港人團體儘快對話,又説正與各持份者溝通,卻從未有人知道審核進度如何、何時由誰進行、考慮了甚麼理據、有何跟進等等,發起聯署的港人組織亦透露市府反應冷淡、接觸極少。我嘗試在欠缺公眾諮詢和決策不透明的質疑聲裏,拼湊出工黨市政府閉門決定拒絕港人聯署的背後過程和考慮。
市府在我提上訴前披露零星電郵,當中的時間印記顯示,時任副市議長 Adele Williams 直到工黨市議員們內部表決 5 日後,方與組織代表開會。最後法庭命令披露文件,原來有市議員同樣狠批「決策完全沒有反映諾定咸香港社群的意見」,佐證了當地港人的批評。現在,我們知道了。
大學從未公開表達對事件的立場,諾定咸市府在平衡人權和商業損失時,從無人知道他們基於甚麼數字作決定。原來大學如此反對,引各項數據在機密影響評估稱每年可損失逾7億港元,擔憂觸怒侮辱寧波當局,遭發留學警示。現在,我們知道了。
看似只是諾定咸內部的紛爭,背後其實牽連甚廣,甚至上升至外交層面。原來隸屬外交部的寧波市政府外事辦公室曾點名港人組織表達憂慮,諾定咸市亦曾向中國駐英大使鄭澤光就港區《國安法》等人權問題提出正式交涉。現在,我們知道了。
知道又可怎樣?披露的資料我留待公眾評判,這個問題我留待讀者和在英港人回答。走筆之際,我也不禁慶幸,儘管在歐洲多國裏,英國資訊自由法例為政府定下最多豁免,但受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保護的知情權至少獲寫入法例。歷來,英國傳媒多番利用《資訊自由法》作調查報道。《每日電訊報》2009年曾獲所有國會議員的開支和報銷,揭發國會濫報開銷成風,有人更曾報銷色情電影,終導致六名國會議員被定罪監禁。
可惜的是,透過法例索取機密文件和政府內部通訊,並由法院作監督,在香港似乎仍然是空中樓閣。香港《公開資料守則》只是行政指引,沒有法律依據,應用上亦相當狹窄,如官員內部討論及意見獲絕對豁免,不需衡量公眾利益。法律改革委員會2013年開始就公開資料進行研究,惟盼港府能儘早設立《資訊自由法》,也確保傳媒進行查冊不受不合理的干預。
調查到此告一段落,謹藉此感謝《追新聞》編輯對我這個毛頭小子的支持和信任。報道包括在英港人的香港人故事和思想,是我們離散傳媒作為新聞工作者不可逃避的責任,也藉此答謝讀者支持。
《追新聞》特約記者Reagan
寫於2025年3月英國
🌟加入YouTube頻道會員支持《追新聞》運作🌟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channel/UC5l18oylJ8o7ihugk4F-3nw/join
《追新聞》無金主,只有您!為訂戶提供驚喜優惠,好讓大家支持本平台,再撐埋黃店。香港訂戶可分享給英國親友使用。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