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國年輕人近日在着名風景區張家界棧道集體跳崖輕生,中國媒體找「專家」分析指大陸00後是典型抑鬱症患者,月薪不過8,000元人民幣,因貧窮走上絕路。學者鍾劍華認為,「全面小康」只不過是政治宣傳伎倆,而中國大陸農村出身的年輕人和民工都在貧窮邊緣狀態生活,「但因為貧窮就自殺就變得好大件事」。
鍾劍華提到《中國青年》雜誌在1980年刊登一封署名潘曉的長信,題為《人生的路呵,怎麼越走越窄》,引發當年文青議論紛紛。潘曉在文章直指小時候聽人講過《雷鋒的日記》、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》,後來經歷文化大革命、四人幫倒台,現實將她擊倒,「甚至我想到過死……心裏真是亂極了」,潘曉後來生活如何就不得而知了。
中國新一代年輕人被稱為「蟻族」、「被割韭要躺平」,以至「人礦」等等創作不同潮語,都是自嘲自己的處境。鍾劍華認為,雖然中國年輕人沒有對社會作出控訴,但這一代人走的路同樣越來越窄,因為他們無辦法主宰自己的命運,在權力支配下看不到前景。反觀香港的年輕一代同樣遭受政權壓迫,他們選擇「跳船」移居海外,與4名「跳崖」的中國年輕人同樣受到打壓,活在「同一天空下」,面對一個壓逼集團,更要敢於揭示社會真相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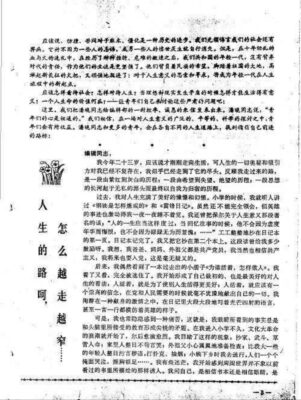
【全文】
潘曉:人生的路啊,怎麼越走越窄?
編輯同志:
我今年23歲,應該說才剛剛走向生活,可人生的一切奧秘和吸引力對我已不復存在,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盡頭。回顧我走過來的路,是一段由紫紅到灰白的歷程;一段由希望到失望、絕望的歷程;一段思想長河起於無私的念頭而終以自我為歸宿的歷程。
過去,我對人生充滿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。小學的時候,聽人講過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》和《雷鋒的日記》。雖然還不能完全領會,但英雄的事跡也激動得我一夜一夜睡不着覺。我還曾把保爾關於人生意義的那段着名的話:「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:當回憶往事的時候,他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,也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羞愧……」工工整整地抄在日記本的第一頁。日記本用完了,我又把它抄在第二個本上。這段話曾給我多少鼓勵啊。我想,我爸爸、媽媽、外祖父都是共產黨員,我當然也相信共產主義,我將來也要入黨,這是毫無疑義的。
後來我偶然看到一本過去出的小冊子《為誰活着,怎樣做人》。我看了又看,完全被迷住了。我開始形成了自己最初的、也是最美好的對人生的看法:人活着,就是為了使別人生活得更美好;人活着,就應該有一個崇高信念,在黨和人民需要的時候就毫不猶豫地獻出自己的一切。我陶醉在一種獻身的激情中,在日記裏大段大段地寫着光芒四射的語言,甚至一言一行都模仿着英雄的樣子。
可是,我也常常隱隱感到一種痛苦,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實總是和頭腦裏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銳的矛盾。在我進入小學不久,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就開始了,而後愈演愈烈。我目睹了這樣的現像:抄家、武鬥、草菅人命;家裡人整日不苟言笑,外祖父小心翼翼地准備檢查;比我大一些的年輕人整日污言穢語,打撲克、抽煙;小姨下鄉時我去送行,人們一個個掩面哭泣,捶胸頓足……我有些迷茫,我開始感到周圍世界並不像以前看過的書裏所描繪的那樣誘人。我問自己,是相信書本還是相信眼睛,是相信師長還是相信自己呢?我很矛盾。但當時我還小,我還不能對這些社會現像進行分析。況且過去的教育賦予了我一種奇怪的能力,這就是學會把眼睛閉上,學會說服自己,學會牢記語錄,躲進自己高尚的心靈裏。可是,後來就不行了。生活的打擊向我撲來。那年我初中畢業,外祖父去世了。一個和睦友愛的家庭突然變得冷酷起來,為了錢的問題吵翻了天。我在外地的母親竟因此拒絕給我寄撫養費,使我不能繼續上學而淪為社會青年。我真是當頭挨了一棒,天呵,親人之間的關系都是這樣,那麼社會上人與人的關系將會怎樣呢?我得了一場重病。病好後,借助幾個好同學的力量,給街道辦事處寫信,得到了同情,被分配在一家集體所有制的小廠裏,開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。那時候,我仍然存在着對真善美的向往,也許家庭的不幸只是一個特殊的情況,我現在已經踏上了生活,生活還是充滿誘惑力的,她在向我招手。
但是,我又一次失望了。
我相信組織,可我給領導提了一條意見,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團的原因……
我求助友誼,可是有一次我犯了一點過失時,我的一個好朋友,竟把我跟她說的知心話悄悄寫成材料上報了領導……
我尋找愛情。我認識了一個幹部子弟。他父親受「四人幫」逼害,處境一直很慘。我把最真摯的愛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撲在他身上,用我自己受傷的心去撫摸他的創傷。有人說,女性是把全部的追求都投入,只有在愛情裏才能獲得生命的支持力。這話不能說沒有道理。盡管我在外面受到打擊,但我有愛情,愛情給了我安慰和幸福。可沒想到,「四人幫」粉碎之後,他翻了身,從此就不再理我……
我躺倒了,兩天兩夜不吃不睡。我憤怒,我煩躁,我心理堵塞得像爆炸一樣。人生啊,你真正露出了醜惡、猙獰的面目,你向我展示的奧秘難道就是這樣!?
為了尋求人生意義的答案,我觀察着人們,我請教了白發蒼蒼的老人,初出茅廬的青年,兢兢業業的師傅,起早摸黑的社員……可沒有一個答案使我滿意。有許多人勸我何必苦思冥想,說,活着就是活着,許多人不明白它,不照樣活得挺好嗎?可我不行,人生、意義,這些字眼,不時在我腦海翻騰,仿佛在我脖子上套着繩索,逼我立即選擇。
我求助人類智慧的寶庫——拼命看書,希望從那裏得到安慰和解答,但看書並沒有使我從苦惱中得到解脫,慢慢地,我平靜了,冷漠了。社會達爾文主義給了我深刻的啟示。人畢竟都是人啊!誰也逃不脫它本身的規律,在利害攸關的時刻,誰都是按照人的本能進行選擇,沒有一個真正虔誠地服從那平日掛在嘴頭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。人都是自私的,不可能有甚麼忘我高尚的人。過去那些宣傳,要麼就是虛偽,要麼就是大大誇大了事實本身。
對人生的看透,使我成了雙重性格的人。一方面我譴責這個庸俗的事實;另一方面,我又隨波逐流。黑格爾說過:「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,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。」這幾乎成了我安撫、平復創傷的名言。我也是人。我不是一個高尚的人,但我是一個合理的人,就像所有的人都是合理的一樣我也掙工資,我也計較獎金,我也學會了奉承,學會了說假話……做着這些時,我內心很痛苦,但一想起黑格爾的話,內心又平靜了。
我體會到這樣一個道理:任何人不管是生存還是創造,都是主觀為自我,客觀為別人。就像太陽發光,首先是自己生存運動的必然現像,照耀萬物,不過是它派生的一種客觀意義而已。所以我想,只要每一個人都盡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價值,那麼整個人類社會的向前發展也成為必然的了。這大概是人的規律,也是生物進化的某種規律——是任何專橫說教都不能淹沒、不能哄騙的規律。
有人說,時代在前進,可我觸不到它有力的臂膀;也有人說世上有一種寬廣的、偉大的事業,可我不知它在哪裏。人生的路呵,怎麼越走越窄,可我一個人已經很累了呀,仿佛只要鬆出一口氣,就意味着徹底滅亡。真的,我偷偷地去看過天主教堂的禮拜,我曾冒出過削發為尼的念頭,甚至我想到過死……心裏真是亂極了,矛盾極了。
編輯同志,我在非常苦惱的情況下給你們寫了這封信,我把這些都披露出來,並不是打算從你們那裏得到甚麼良方妙藥,如果你們敢於發表它,我倒願意讓全國的青年看看。我相信青年們心是相通的,也許我能從他們那裏得到幫助。
潘曉
1980年4月



